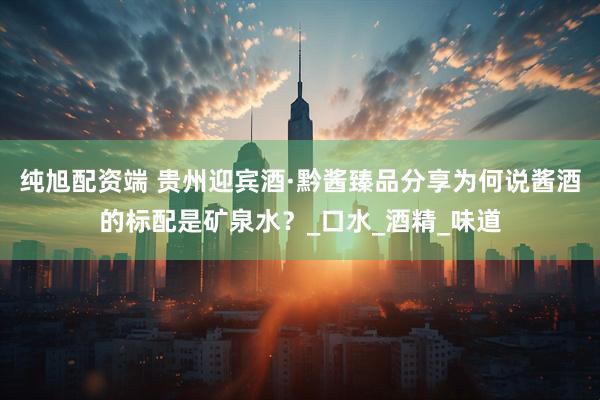村口老槐树的影子刚斜斜铺到晒谷场,麦芽糖的甜香就漫过了集市的竹篱笆。刘老汉的糖担支在最显眼的位置,两只竹筐里码着琥珀色的糖块,像浸在蜜里的冻石,竹扁担还留着经年累月压出的浅痕。他总在袖口搭块蓝布,见人来就掀开盖着糖块的棉絮,甜香便顺着指缝涌出来广信配资,粘住了赶集人匆匆的脚步。
“要块敲得碎的!”穿花布衫的妇人递过五毛钱,刘老汉操起小铜锤,对着糖块边缘轻轻一敲,“啪”的一声脆响,碎糖渣落在油纸袋里,像撒了把碎金子。妇人捏起一小块塞进孙子嘴里,孩子的腮帮子立刻鼓起来,含糊地喊着“还要”,糖丝从嘴角牵出来,在晨光里闪着亮。
我总爱蹲在糖担旁看他熬糖。大铁锅里的麦芽浆咕嘟咕嘟翻着泡,泡沫边缘泛着焦黄色,刘老汉用长柄木勺搅着广信配资,糖浆在勺底挂成透明的丝,滴进冷水里“啪”地凝成珠。“得用清明前的新麦,”他额头的汗珠滚进花白的胡子里,“出糖率高,甜得正。”旁边卖菜的张婶凑过来看:“给我留块整的,孙子明天过生日。”刘老汉点点头,往锅里撒了把桂花,甜香里立刻掺了点清冽的草木气。
有个穿中山装的老人,每周都来买两块糖。他不讨价还价,只让刘老汉把糖纸包得方方正正,揣进上衣内袋。有回我见他坐在老槐树下,慢慢剥开糖纸,把糖块凑近鼻子闻了闻,却没吃,只对着集市入口的方向望。后来才知道,他年轻时在镇上教书,妻子总在赶集日给他送麦芽糖,“她熬的糖里,会掺点橘子皮。”老人的声音很轻,糖块在手里慢慢化了,粘住了指腹。
展开剩余58%孩童们围着糖担时最热闹。他们攥着皱巴巴的角票,踮着脚看竹筐里的糖块,有人指着最大的那块咽口水,有人被铜锤敲糖的声音吓得往后缩。刘老汉从不赶他们广信配资,有时还会捏点碎糖渣,分给没带钱的孩子。“我家小子小时候,也总在糖担前挪不动脚。”他笑着说,木勺在锅里划出圈,糖浆的丝缠在勺柄上,像系着根看不见的线。
暴雨突至的集市,糖担躲进了祠堂的屋檐下。刘老汉把棉絮盖得更严实,却还是有雨水打湿了竹筐边角,糖块吸了潮气,变得软黏黏的。穿雨衣的妇人冲进来:“给我来三块!孩子发烧了,就想吃这个。”刘老汉用布擦干糖块,额外多敲了些碎渣,“趁热吃,发点汗就好了。”雨声噼里啪啦打在祠堂的瓦上,混着麦芽糖的甜香,竟有了点安稳的暖意。
深秋的集市渐渐冷清,刘老汉的糖担旁堆起了南瓜和红薯。有天我看见他的儿子来帮忙,年轻人嫌铜锤敲着费劲,想用电锯,被刘老汉瞪了回去:“敲糖得有轻重,急了就失了味。”儿子撇撇嘴,却还是学着用铜锤轻轻敲,糖块裂开的声音里,有阳光落在竹筐上,把糖块照得半透明,像块凝固的琥珀。
散集时,刘老汉收拾糖担的动作很慢。他把铜锤擦得锃亮,放进竹筐角落,又将沾了糖渣的棉絮抖了抖。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,和糖担的影子叠在一起,像幅泛黄的画。远处传来孩童的欢笑声,大概是刚买到糖的孩子在奔跑,甜香追着他们的脚步,漫过晒谷场,漫过老槐树,漫过那些被糖香浸软的旧时光。
后来每次路过集市,我总忍不住往老槐树下望。刘老汉的糖担还在,只是旁边多了个年轻的身影,正学着用木勺搅糖浆。风吹过竹筐,棉絮轻轻动了动,甜香依旧漫得很远,像谁在低声讲着故事,故事里有桂花的香,有铜锤的响,还有无数双捧着糖块的手,在岁月里慢慢握住了温柔。
发布于:湖北省尚红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